谢国忠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,其对楼市的预判始终是市场关注的焦点,这位以“唱空”楼市闻名的学者,在过去二十年间多次公开表达对中国房价泡沫的担忧,其观点既有严谨的经济学逻辑,也夹杂着对政策与市场关系的深刻洞察,理解谢国忠的房价理论,不仅需要拆解其核心论点,更需要结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与现实,才能看清其预判背后的逻辑脉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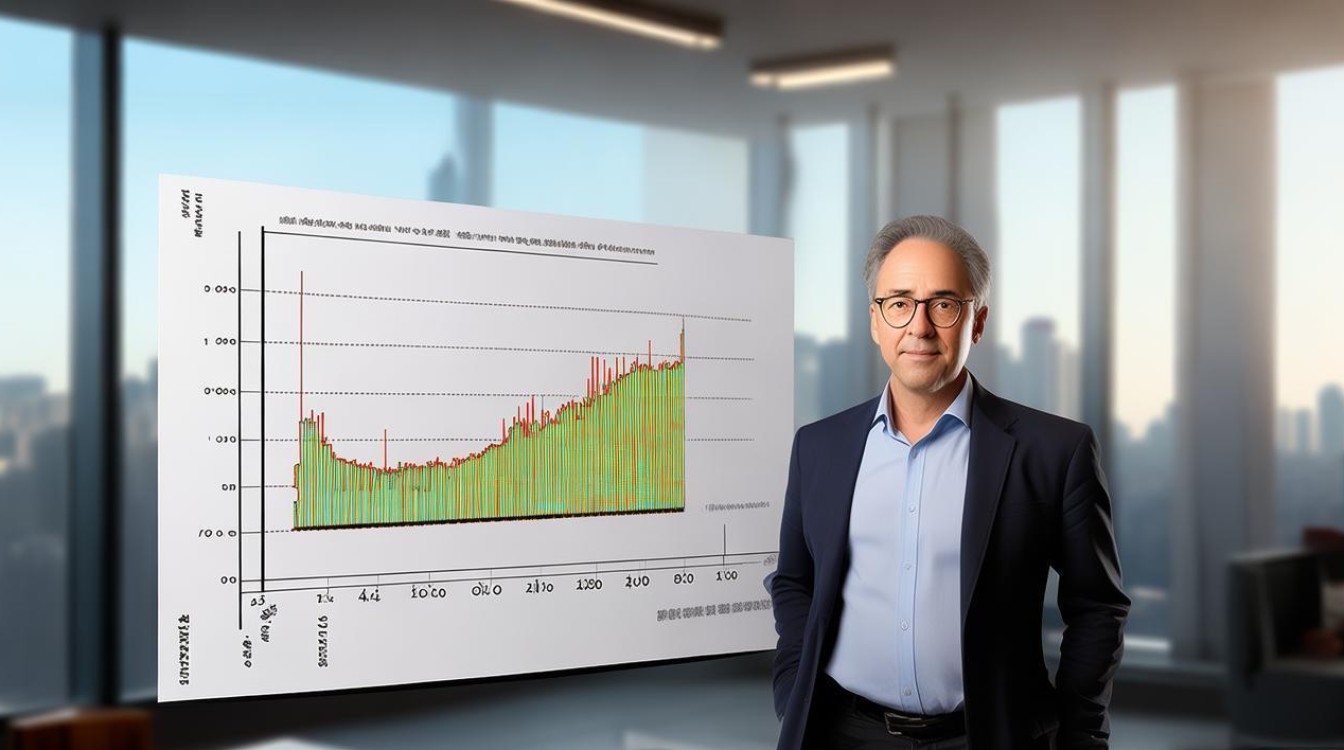
泡沫本质: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
谢国忠对房价的核心判断,始终围绕“泡沫”展开,他认为,中国房价早已脱离居住属性的基本面,演变为一种由投机需求驱动的金融资产泡沫,在其代表作《再见,房价》一书中,他明确提出:“房价的本质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现,但当房价上涨的预期成为唯一支撑,现金流本身已无法覆盖成本时,泡沫便已形成。”
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是两大关键指标: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,谢国忠多次引用国际经验指出,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保持在3-6倍之间,而中国一线城市(如深圳、上海)这一比例在2020年前后普遍超过35倍,部分核心区域甚至高达50倍,租售比同样偏离合理区间——国际上健康的租售比通常在1:200至1:300之间(即月租金约为房价的0.3%-0.5%),而中国主要城市的租售比普遍低于1:500,部分城市甚至低至1:1000,这意味着依靠租金回收投资成本需要80年以上,远超资产合理回报周期。
谢国忠强调,这种背离并非由真实居住需求推动,而是源于“货币超发+土地财政”的双重驱动,2008年金融危机后,中国为刺激经济实施“四万亿”计划,货币供应量(M2)从47万亿元飙升至2022年的266万亿元,大量资金通过银行信贷、影子银行等渠道流入楼市,形成“资产荒”下的投机热潮,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金补充财政,202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8.7万亿元,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5%,这种“土地财政依赖症”导致地方政府有动机维持高地价,进而推高房价预期,形成“地价→房价→财政”的循环。
供需矛盾:被高估的需求与被垄断的供给
在谢国忠看来,中国楼市的供需结构存在根本性扭曲,需求端被城镇化进程和投机需求过度夸大,供给端则因土地垄断导致供给弹性不足,二者共同推高房价。
关于需求端,他质疑“城镇化必然推高房价”的主流观点,数据显示,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.22%提升至2022年的65.22%,但增速已明显放缓——2010-2020年年均提升1.3个百分点,较2000-2010年下降0.5个百分点,更重要的是,城镇化带来的新增需求更多是“农民工市民化”,这部分群体购房能力有限,实际购房占比不足20%,真正的需求主力是城市改善型需求和投机需求,前者在住房饱和度提升后逐渐减弱,后者则因房价上涨预期而持续涌入,形成“追涨杀跌”的投机泡沫。
供给端的问题则指向土地制度,中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,地方政府通过“招拍挂”垄断土地供应,且倾向于通过控制土地投放节奏维持高地价,谢国忠指出,这种垄断导致土地供给无法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,尤其是一线城市,虽然人口持续流入,但土地供应长期受限,加剧了供需紧张,北京、上海的土地面积分别占全国面积的0.18%和0.06%,但贡献了全国10%以上的GDP,土地供给不足与经济人口不匹配的矛盾,成为高房价的制度根源。
为更直观展示供需矛盾,可通过下表对比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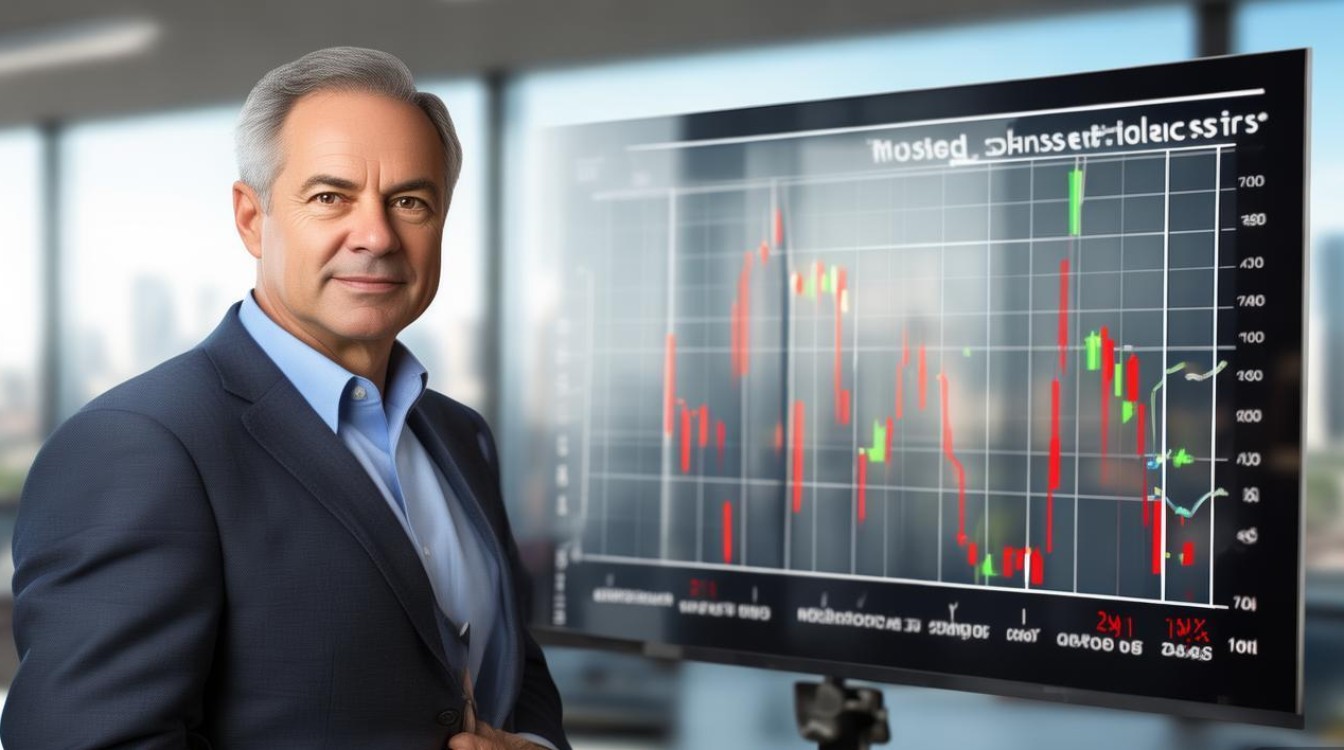
| 指标 | 中国主要城市(2022年) | 国际合理水平 |
|---|---|---|
| 房价收入比 | 25-35倍 | 3-6倍 |
|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| 8平方米 | 30-35平方米 |
| 土地财政依赖度 | 30%-40%(地方政府) | <10% |
| 投机性购房占比 | 约35%(二手房市场) | <10% |
政策依赖:刺激与调控的循环困境
谢国忠对政策调控的效果持悲观态度,认为中国楼市已形成“政策刺激-泡沫膨胀-政策收紧-市场调整”的循环,且每次刺激后的反弹幅度均超过前一次,泡沫风险持续累积。
他特别批评2008年后的“四万亿”计划和2015-2016年的“棚改货币化”政策,前者通过宽松信贷释放天量流动性,导致房价在2009-2010年暴涨50%以上;后者通过PSL(抵押补充贷款)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,用于棚改货币化安置,直接催生了三四线城市的“涨价去库存”,部分城市房价在两年内翻倍,谢国忠指出,这类政策虽短期稳定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,却将风险向后转移——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08年的17.9%升至2022年的63.3%,远超国际警戒线(60%),且大部分债务集中于房地产领域。
对于“房住不炒”的调控政策,谢国忠认为其治标不治本,限购、限贷、限价等行政手段虽能短期抑制投机,但未触及土地垄断和货币超发的根源,一旦政策放松,房价便迅速反弹,2019-2021年部分城市因“因城施策”放松调控,房价再度出现明显上涨,他警告:“调控就像给高烧病人吃退烧药,暂时退烧但病因未除,最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。”
全球视角:中国房价泡沫的历史参照
谢国忠常将中国楼市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、2000年代的美国进行比较,认为中国房价泡沫的特征与历史案例高度相似,破裂风险不容忽视。
以日本为例,1985年“广场协议”后,日元大幅升值,日本央行为刺激经济实行宽松货币政策,大量资金流入楼市和股市,导致东京、大阪等城市房价在5年内上涨3倍以上,当时日本同样认为“土地稀缺”“城镇化持续推进”,房价不会下跌,但1990年泡沫破裂后,日本房价暴跌60%以上,至今未恢复至峰值水平,银行坏账激增,经济陷入“失去的三十年”。
谢国忠指出,中国与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:货币超发推动资产泡沫、人口结构即将迎来拐点(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22年达14.9%,进入深度老龄化)、居民部门杠杆率过高,不同之处在于,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更强,可通过“保交楼”、限价政策等短期稳定市场,但这并未改变泡沫的本质,反而可能延长调整周期,他警告:“泡沫破裂的时间无法预测,但破裂是必然的,只是以何种方式——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——取决于政策应对。”
现实启示:回归理性还是等待破裂?
谢国忠的房价预判虽被部分人视为“危言耸听”,但其对泡沫风险的警示值得深思,2021年以来,中国楼市进入深度调整期,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腰斩,部分房企(如恒大、碧桂园)出现债务违约,房价在一线城市以下城市普遍下跌10%-20%,这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“泡沫存在”的判断。

中国楼市的复杂性远超简单的历史类比,与日本、美国不同,中国城镇化仍有空间(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7.7%),居民储蓄率较高(2022年为36.8%),且政策工具箱充足(如“保交楼”专项借款、房企融资“三支箭”),这些因素可能使房价调整以“缓慢阴跌”而非“断崖式下跌”的方式展开,实现“软着陆”。
但无论如何,谢国忠的观点提醒我们:房价脱离基本面是不可持续的,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市场参与者,都需要警惕过度依赖房地产的风险,正如他所说:“房地产可以成为经济的助推器,但绝不能成为经济的发动机。”只有推动住房回归居住属性,建立“多主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”的住房制度,才能避免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。
相关问答FAQs
问题1:谢国忠曾预测“中国房价将在未来5年内出现30%-50%的调整”,这一预判是否可能实现?
解答:谢国忠的这一预判基于“泡沫破裂”的逻辑,但实现概率受政策调控力度和经济环境影响,当前中国已出台“保交楼”、房企债务重组、限购限贷松绑等政策,短期内房价“硬着陆”风险较低,但从长期看,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、人口老龄化加速,房价存在理性回调压力,30%-50%的调整幅度在部分三四线城市可能逐步显现,但一线城市因资源集中,调整幅度或相对有限。
问题2:如何看待谢国忠“房价回归居住属性”的观点?这一观点在中国楼市实现难度如何?
解答:“房价回归居住属性”意味着房价由居民收入和租金水平决定,而非投机需求,实现这一目标需打破土地财政依赖、增加保障房供给、抑制投机性购房,当前政策已明确“房住不炒”,但土地垄断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,且居民财富与房地产深度绑定(房产占居民资产比重达70%),导致房价调整面临阻力,回归居住属性是一个长期过程,需通过房产税、土地制度改革等综合政策推进,短期内难以完全实现。


